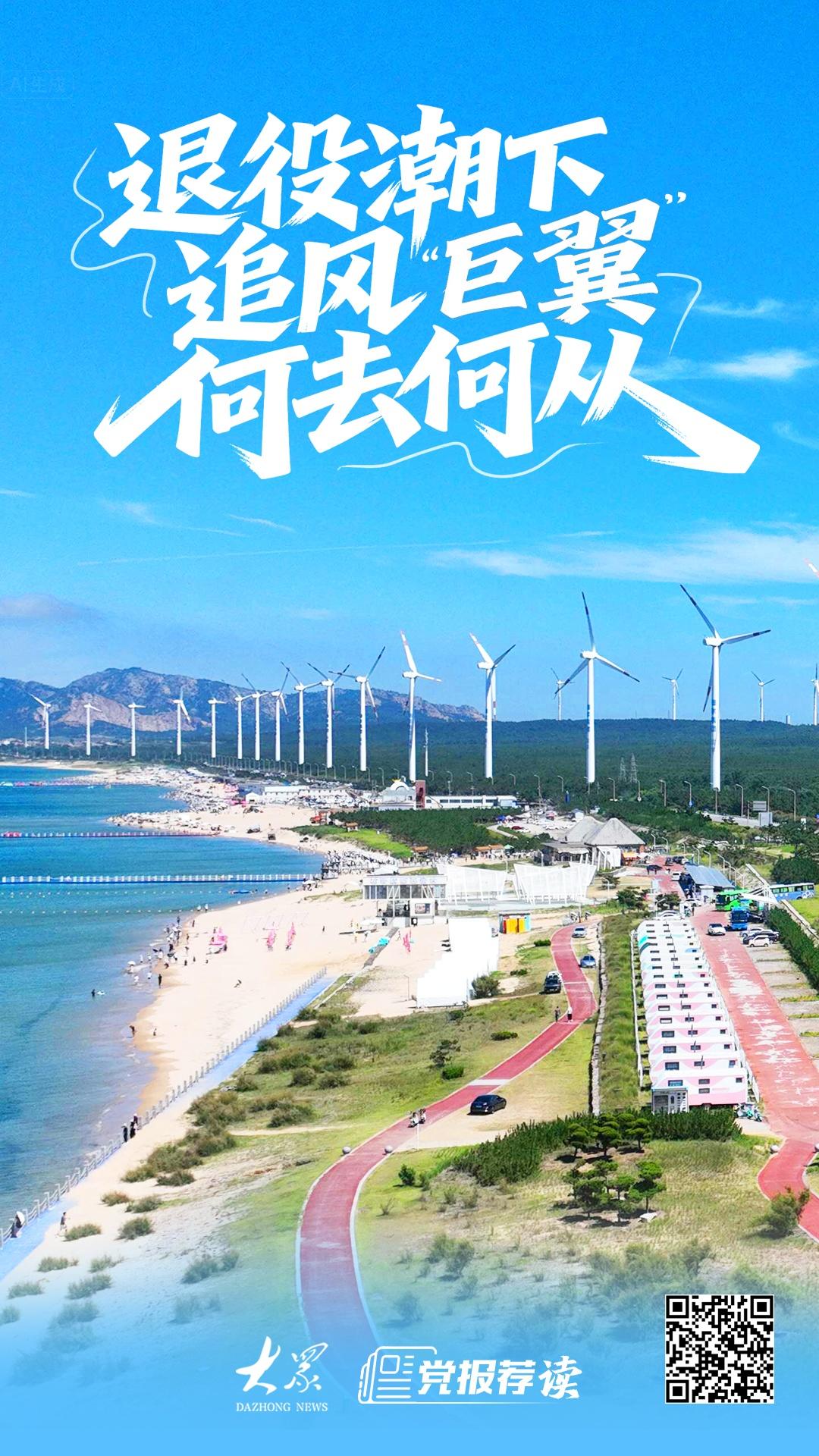
隨著早期投運的風電裝備逐步“退休”,我國將迎來風電機組退役高峰期
退役潮下,追風“巨翼”何去何從
不久前,位于濰坊的中廣核臨朐劉王莊風電場內,一臺已持續運轉超過15年的風電機組葉輪從六十余米高空緩緩吊下,標志著該風電場“以大代小”煥新行動正式開始。
此次被拆除的0.85MW風電機組共45臺,屬于國內較早一批投入運營的風電裝備。取而代之的是15臺新一代智能風機,總裝機容量從38.25MW躍升至112.5MW。

隨著早期投運的風電裝備逐步“退休”,我國將迎來風電機組退役高峰期。
山東風電裝機規模居全國前列,當大規模退役潮來臨,這些追風“巨翼”該何去何從?山東企業又該如何搶抓機遇,率先破局?記者近日展開了采訪。

一道必答題
大規模退役潮來臨,傳統處理方法難以為繼,“包袱”如何轉化為財富?
駕車穿行野外,常會遇見巍巍矗立的風力發電機。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些碩大無比的設備并非安裝后就一勞永逸。

一般而言,風力發電機組的設計使用壽命為20-25年。2006年,中國風電迎來規模化發展起點。以此推算,2025年起,我國將迎來風機退役高峰期。有專業機構統計,到2030年我國預計將有超過3萬臺風電機組退役,產生的固體廢物總量將突破300萬噸,其中退役風機葉片重量將突破50萬噸。
截至今年7月底,山東風電裝機2749萬千瓦。這一數字還在不斷擴大,今年山東計劃新增海上風電300萬千瓦。
全國范圍來看更是如此,未來退役的風機裝備遠遠不止目前的“存量”。今年9月份,我國提出到2035年,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爭達到36億千瓦。
“以大換小”政策也將直接增加退役風電設備數量。2023年6月,國家能源局發布《風電場改造升級和退役管理辦法》,提出鼓勵并網運行超過15年或單機容量小于1.5兆瓦的風電場開展改造升級。這為初代風機的批量退役按下了“加速鍵”。
不只是中國,風機大規模退役是全球主要風電市場共同面臨的問題。在風電退役規模尚小時,堆砌、掩埋、焚燒曾是全球處理退役風機(尤其是葉片)的主流方式。然而,當大規模退役潮來臨,傳統方法難以為繼。
舉例來說,一個總裝機規模20萬千瓦、單臺風機容量5兆瓦、單個葉片重20噸的風電場,風機全部退役后,僅葉片總重量就達2400噸。如果將其平鋪擺放,占地面積比3個足球場還大。
無論是堆砌、掩埋對土地資源的占用,還是焚燒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都與風電綠色發展的初衷背道而馳。
如何妥善處理退役風機裝備、把“包袱”轉化為財富,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必答題。

“最難啃的骨頭”
葉片兼顧高強度和輕量化,存在原材料難回收、運輸成本高、履責主體模糊等困難
在江蘇一家企業廠房內,各種不同型號的風機葉片正在進行揮舞和擺振實驗。和普通葉片不同,這種葉片是“可回收”的,到達使用年限后,可以將玻璃纖維與樹脂進行分離,其中玻璃纖維回收率可以達到85%。
今年3月,該企業生產的全國首套可回收風電葉片已經運往風電場投入應用。
這種新型葉片有什么奧妙?關鍵是其采用了可回收熱固性樹脂。傳統葉片采用的環氧樹脂,像強力膠將各個零部件黏住,一旦成型后不可逆轉。
透過這項技術新突破,就不難理解當前傳統風機裝備回收面臨的技術困境。
實際上,退役風機拆解后,不同部件的回收利用難度有著顯著差異。
風電機組主要由塔架、機艙、輪轂和葉片構成,其中塔架、輪轂等材質以鋼鐵為主,機艙內的發電機、齒輪箱等核心部件也不難實現二次利用。
葉片因需要在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中承受風吹日曬的考驗,所以普遍采用玻璃纖維增強復合材料制成,部分海上風電或大功率機型還會使用性能更優的碳纖維復合材料。材料的特殊性,讓葉片成為“最難啃的骨頭”。
風機葉片運輸難,也對最前端的葉片拆解環節造成影響。風電場大多地處偏遠地區,受交通條件限制,一套新的風電機組運輸成本往往以十萬元計,如果退役后再次完整運輸,這筆賬顯然劃不來。
比技術難題更棘手的,還有當前產業鏈存在的“責任真空”。早期風電項目開發時,行業普遍存在“重裝機、輕處置”傾向,多數項目未在合同中明確葉片退役后的責任主體,各方處理積極性不足。
2023年印發的《關于促進退役風電、光伏設備循環利用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督促指導集中式風電和光伏發電企業依法承擔退役新能源設備(含零部件)處理責任。“政策層面雖有框架性要求,但責任主體履責規范、環節分工等細則缺失,仍需要細化履責流程,讓‘誰來做、怎么做、做不好怎么辦’有清晰依據。”北京計鵬信息咨詢有限公司技術總監朱燕嵩說。

關鍵技術破冰
葉片回收處置行業處于從“無害化處理”向“高價化利用”轉型初期
前不久,在煙臺某海洋牧場的海域上,一座特殊的人工魚礁緩緩吊入海底——這座魚礁的主體并非傳統混凝土,而是由退役風機葉片材料制作而成,底座則加入了葉片粉碎后的再生材料。投入使用后,這片“人造家園”迅速成為浮游生物的聚集區。
這是中車山東風電有限公司作出的新嘗試,實現了新型固廢到海洋新材料的應用。

“相比混凝土材料,用回收的風機葉片成本更低。”經過了一系列安全性、可靠性檢測及海洋試驗,中車山東風電有限公司退役風機業務技術主任董國慶驚喜地發現,新型人工魚礁附著性更好。
作為國內風電裝備制造領域的龍頭企業,該公司早在五年前就啟動了退役風機葉片回收利用的布局,成功研發“退役葉片高效智能處理成套裝備”,打造了國內首套“智能移動工廠”。
該移動工廠大小與標準集裝箱差不多,可直接進駐風場或葉片貯存地,通過“分散式預處理+集中式深度加工”的雙模式運作,突破傳統固定式處理產線的局限,極大提升規模化作業效率。
實際上,梳理目前行業實踐,退役風機葉片的回收處理已形成多層級技術路徑。
梯次利用被普遍視為優先選項。無結構性損傷、狀態良好的退役葉片可優先作為風機備件重新“上崗”。
資源化回收技術分為物理法與化學法兩大類。簡單來說,物理法就是只改變葉片的物理形態,化學法則是利用高溫或者化學溶劑,把玻璃纖維和樹脂分開,然后再分別進行回收。
物理法因技術成熟、二次污染比較少,是當前市場主導的處置路徑。
“我們研發的這套設備就是采用物理法,通過切割、分拆后把葉片破碎成再生纖維。”董國慶說,這種再生纖維作為增強材料可以運用到高抗裂混凝土、抹面砂漿、自流平砂漿等工程中,展現出優異性能。
盡管市場前景廣闊,一批企業不斷推動技術更新迭代,但葉片回收處置行業仍處于從“無害化處理”向“高價化利用”轉型初期。

還要跨過多道門檻
從“環保負擔”到“資源富礦”,單憑技術突破遠遠不夠
新興市場吸引著眾多企業競相角逐。近幾年朱燕嵩接觸到的意圖布局退役風機葉片循環利用的企業或單位數量眾多,不僅有本領域企業,還有些跨領域的單位。
這源于“十四五”期間國家的重視和政策推動。2024年10月,山東印發方案,提出要建立健全風電和光伏發電企業退役設備處理責任機制,探索建立風電、光伏設備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探索開展風電光伏領域高端裝備再制造。
不過,要讓退役風機葉片真正完成從“環保負擔”到“資源富礦”的轉變,除了技術突破,還要跨過多道門檻。
新興產業的起步階段往往都伴隨著“野蠻生長”的陣痛。不止一位受訪者透露,當前風機葉片回收利用受“小作坊”的沖擊尤為突出,擠壓了正規企業的回收來源。
風機葉片作為工業固廢,發電企業需付費委托處理。小作坊往往通過非法拆解、隨意處置的方式降低成本,兩三百元一噸就能承接業務;反觀正規再生利用企業,每噸處置費用高達幾千元。這種懸殊的價格差,導致了“劣幣驅逐良幣”。
朱燕嵩回憶,2021-2022年,風機葉片回收行業熱度初顯時,處置費用每噸約在4000-5000元,這幾年價格呈持續下降態勢,處置費每噸在2000元左右,甚至更低。“對部分已投入大量研發和成套產線的企業來說,降低價格也得收,不然虧損更多。”
這無疑打擊了拿真金白銀投入研發的企業的積極性。山東省循環經濟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忠蓮建議,可以建立物聯網溯源監管平臺,運用大數據、二維碼等技術實現全生命周期監控,根治“劣幣驅逐良幣”亂象。
回收體系的建立也面臨諸多現實障礙。由于大多數退役風力發電機組屬于各發電集團的國有資產,尤其是通過“以大代小”項目退下來的設備,國有資產屬性、賬面資產與實際價值差異大等現實問題難以有效解決,從而造成資產閑置。
“建議有關部門盡快統一安全評估標準、細化評估指標、檢測方法、合格閾值,消除企業處置顧慮;鼓勵國有企業優化完善內部配套流程,提升處置合規性與效率,為閑置資產合規、順暢進入循環市場掃清障礙。”朱燕嵩說。
行業發展協同機制仍需進一步完善。張忠蓮認為,長久來看,風光設備回收將走向與家用電器相似的生產者責任制,需要進一步正確引導,同時盡快完善落實行業標準、技術規范、認證體系等,建立起合理的商業模式。
“山東有責任也有能力為新能源設備回收利用探路先行。”張忠蓮說,山東應搶抓機遇,分領域、分區域培育引領性企業,支持建設風電光伏設備循環利用產業集聚區,為即將到來的退役潮打好產業基礎,進一步夯實綠色發展底色。
來源:大眾新聞·大眾日報
編輯:李新花 李婕寧
一審:賈春毅
二審:孫瑞永
三審:管延會















